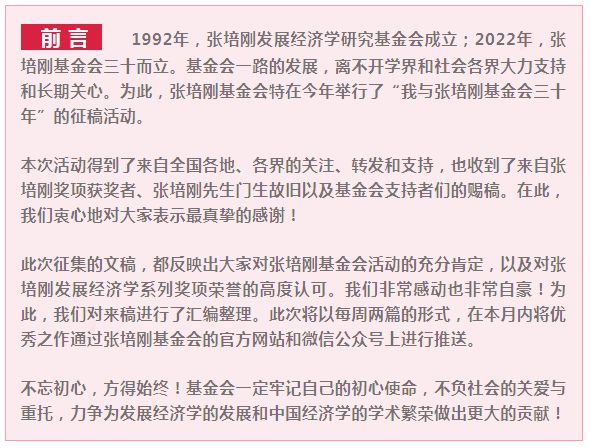
传承张培刚
2022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庆祝建会30周年。张先生的夫人谭慧老师现为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端午节假期发我一条微信:“你是张老师的传人,写一篇短文以示纪念!”看得我心头一热,当即作答:“朱玲遵命”。只见一连串“微表情”飞了过来: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有微笑、作揖和鲜花。好可爱的谭老师哟!
一、导师的导师
我和张培刚先生(1913-2011)的师承关系源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曾启贤(1921-1989)。1978年,我从西北大学考到曾老师名下攻读硕士学位。进校不久便听曾老师骄傲地讲述,他的硕士导师是张培刚。张先生的博士论文曾获1946-1947年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论文还因富有创见而列入《哈佛经济丛书》。这番故事顿时令我们一众同学对张先生“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曾老师欣然许诺:“张先生在华工(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们见见!”
机会在我们完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之后来临,曾老师把张先生请来给研究生班启蒙微观经济学。那时我们都知晓张先生经历坎坷,没想到他的面容似乎未留苦难的痕迹,而是笑嘻嘻地一脸童趣。他衣着得体而舒适,动作轻盈而儒雅,走上讲台如见熟人一般跟听众打声招呼,刹那间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张先生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用连吃四五碗热干面的感觉,讲解边际效用递减的道理;又用湖北省以往填湖种粮的后果,说明什么是资源配置不当。他边讲边写,板书大方美观,笔画入木三分。说到精彩之处抬手就作图,曲线坐标勾勒迅速,还不用米尺圆规。每逢下课我都觉得意犹未尽,怀疑时间增添了加速器。多年后,我还写给基金会秘书黄莉(2014年10月27日):“张先生的启蒙是如此生动,到如今脑海里还有他鲜活的授课影像。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相机随时拍下来。”
在校时,我注意到曾老师家门口贴了张纸条:“敬谢闲谈”。可想而知,导师的时间有多宝贵。那导师的导师呢?我就更不该去打扰了!所以,虽则一直崇敬张先生,我却不曾去“追星”。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经济所)工作至今。其中,1983-1988年间在联邦德国深造,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于1986年回国做农户调查。那时曾老师但凡到北京出差,经济所所长董辅礽老师(1927-2004)就会请他用餐并让我作陪,席间少不了谈及张先生近况。武大校友陈端洁来所里收集文献资料,也曾提到张先生和曾老师如何相互指导对方的学生。因此,尽管远离张先生,我对他从未感到陌生。
二、走近张先生
让我自然而然“走近”张先生的契机,是2014年夏日来自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一个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用我那本《减贫与包容: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评奖,我自是深表荣幸。此后忙于组织社保调查和执行交办任务,也无暇顾及评选结果。收到获奖通知时,欣喜还是涌出心底,因为我将专程前往武大,以此告慰曾老师和张先生(参见基金会转载经济所网页2014年10月29日消息:《朱玲获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http://pkcjjh.org/view/871.html)。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0月25-26日举行,由华中科技大学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华科大经济学院和基金会的安排周到温馨,给每位外地与会者选派了向导,陪伴我的联系人是学生小颜。其实,武汉的方言、食品和桂花香于我一如既往地熟悉。与宋德勇教授、张建华教授和黄莉秘书聊天分外亲切,与张先生的女弟子汪小勤教授更是一见如故。跟谭慧老师会面则留给我难忘的感动。那时她已年届耄耋(1930年生人),会议前一天竟在女儿张鹃陪同下来到校园宾馆,逐一敲开与会者下榻的房门予以问候。

颁奖礼之后,谭慧老师拉着我的手细问张先生给我们研究生班授课的情况。提到我的导师曾启贤,连说:“太可惜了!他突然去世对张先生打击很大”。还问起我的校友陈端洁,言明:“张先生为她评审过学位论文呀!”我由衷赞道:“端洁好福气,得到张老师的指导!我们班同学也好运气,得到张老师的启蒙。”谭老师轻叹:“张老师的运气太不好了,提起来都满心酸!这辈子只写了本《农业与工业化》,后来就没机会做什么研究了。”我不忍见她伤悲,缓缓地宽慰:“好在张老师桃李满天下,看看今天这么多人,不都是因为敬仰张老师的人品学问才来的吗?”谭老师默默地点头,沉郁的神色令人痛心不已。回京当晚,我即写邮件感谢基金会成员的辛勤劳作和惠赠《张培刚传》。翻看传记画册,一眼瞥见曾老师和董老师与张先生的合影,更加感念前辈的培养和提携。阅读中,我亦对张先生的学术理想和研究路径高度认同。
首先,他毕生追求“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若无这一坚定的信念,怎能在常年搞基建、受审查、挨批判、养牛送肥却偏偏不能做学问的煎熬中百折不挠,又怎能老骥伏枥在一所理工科院校创建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
其次,注重文献分析、实地调查和理论推演相结合。1934-1941年间,张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这个机构正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创始所长陶孟和先生奠定了调查立所的优良传统。张先生进所后,一方面参与整理保定调查资料,一方面到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的乡村城镇做补充调查。六年间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粮食之运销》3部专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在多种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这些工作,为他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凝聚了坚实的基础。
如此看来,我和我的团队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采取的方法与张先生一脉相承。我们不仅探索中国经济如何转型,而且关注怎样通过制度变革和公共服务供给,保障穷人、妇女、老人、残疾人和少数族群等脆弱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这个视角,追踪调查农村贫困群体、迁移劳动者(农民工)、女性和少数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通过田野工作确认他们最紧迫的需求,评估现有的发展计划、扶贫项目和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并提出备选的政策改善方案。可以说,我们团队的工作融入了包括张先生在内的经济所前辈留下的学术传统。
三、领略张培刚
2019年5月,经济所举办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学部委员、时任所长高培勇牵头,于前一年着手准备庆典,邀请昔日“所友”及亲属与会。谭慧老师由于健康原因不便赴京,指名要我代读贺信。一位课题组伙伴幽默地评说:“这是正式召唤你认祖归宗啊!”会议前三天收到谭慧老师的文稿,我只觉满纸锦绣,叹服那词章情深、文采斐然!文章既慨然回顾张先生的成长环境和学术历程,也明晰道出他与经济所的历史渊源及现实交往,还处处展现了他百折不悔的爱国情怀和坚忍不拔的人生追求。末尾又顺理成章地介绍了基金会的宗旨和活动,重锤击鼓一般地点明,张先生毕生倡导“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勾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蓝图。”(参见谭慧:《薪火相传,勾画中国经济学发展蓝图》,http://econ.cssn.cn/jjx/jjx_ttyw/201905/t20190517_4897474.shtml)。这封贺信我不只看过一遍,每次阅读都能感受谭老师对后辈学者传承和发扬张培刚学术思想的殷切期望。
我们团队自2018年初从事城乡融合发展专题研究,大家在文献学习中不谋而合地精读、讨论和领会张先生的论著。年轻成员金成武从分析“农业现代化在工业化中的关键作用”入手,结合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现实,重新审视围绕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多种学说,探寻勾连与融合不同学说的基础线索。他在论文中注明,张培刚的专著(1949)“首次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基于对张培刚学说的理解,他还把工业化转型的定义引申为:“包含了将传统农业生产部门转变成为一个工业生产部门的过程”(参见金成武,2019:《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经济研究》第8期)。
我也曾借助比较研究介绍和传播张先生的洞见。2018-2019年间,我应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Christine Wong教授(中文名:黄佩华)之邀,连续两个冬季学期(澳洲8-10月)作为“Asian Scholar”(亚洲学者)参与中心的教研活动。她提前列出了每一讲的主题, 2019年增加一讲:“China's challenge to mod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国对经济发展范式的挑战)。为了弄清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对中国的观察及分析,我一面请助教俞蕾从墨大图书馆下载文献;一面写邮件拜托经济所团队年轻成员何伟收集统计数据并制作图表。自己则用google scholar检索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培刚博士论文,还搜寻到Fukuyama(福山)涉及发展范式的文章和“播客”。历经一番紧锣密鼓的阅读和写作,我总算如期完成课堂演示大纲,在讲授和问答中还颇为享受教学相长的愉悦。准备这一讲时列出的几处要点至今印象深刻:
第一,Naughton用流畅简洁的文字,把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带来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的过程定义为经济发展。(参见:Barry Naughton, 2018, The Chinese Economy:Adaptation and Growth, The MIT Press.)
第二,张培刚在70多年前精准地提炼和列举了农业国转型的条件或曰发展的要素(人口和经济规模及构成、资源种类和数量及地理分布、社会制度安排、技术创新和应用、企业进取精神等等)。他尤其强调,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在于城市和乡村社会都发生工业化。工业化不仅是制造业的机械化,还包括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的现代化。(参见:Pei-Kang Chang, 1949,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出乎一些理论家的意外,并非因为中国的实践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有缺陷。Rodrik一语中的:这些理论家根据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设定的经济起飞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太高了!增长和发展是长期演变的一部分,成功突破贫困陷阱的经济体,是那些根据本土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做出恰当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参见:Dani Rodrik,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四,Fukuyama曾在《历史的终结?》一文断言,随着东欧、中国和苏联改革的进展,两大制度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然完结。这并非意味历史的进步抵达终点,而是表明,世界上还未出现比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政治相结合更为妥当的替代性制度选择(参见:Francis Fukuyama, 1989,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论断操之过急,Fukuyama在文章发表后又陆续追加了不少解释。例如,他在1992年补充道,民主既不会一蹴而就地成为整个世界的特征,也未必会延展到所有地方。2018年,他又在“播客”说明,他早前的理论聚焦于民主制度,对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中性国家”作用未给予充分关注。中国恰恰具备“一个相对中性国家”的能力,其制度模式及现有表现对历史终结之说形成了最大的挑战。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还是一个问题。
第五,Acemoglu和Robinson对国家制度安排的分类别具一格:一类为“包容型”,另一类为“攫取型”。构建包容型的经济制度首先需要安全的财产权利和广泛分布的经济机会,这是激励人们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的前提。其次,权力既受到限制又广泛分配,这是引发创造性破坏和技术创新、进而导致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言而喻,攫取型的制度安排恰为包容型的反面。对于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用包容型替代攫取型的制度可谓转型成功的关键。非洲大陆既有成功转型的典型,也有失败的案例,为改革与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ers.)
纵观几位思想者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说,我一是惊叹张培刚的思想穿透力,他睿智地阐明,发展的要素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可有不同的组合,此时恰当彼时未必如此。我在课堂上还评论,那些把中国的发展路径视为异类的理论家,多半缺少这种动态思维,或者以为发展实践非白即黑,忘记了灰色地带存在的可能性。二是这几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不以一时论短长。这无疑发人警醒: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的转型尚未结束,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社会实乃任重道远。作为发展经济学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自然也永无止境。
四、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团队不仅关切疫区亲朋好友的境况,而且也渴望知晓疫情对农户和迁移劳动者生计的影响,还想了解他们应对灾害打击的策略和获得的公共支持,以便弄清涉及这一群体的社会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板。2021年3月疫情走向低谷,我们赶紧启动湖北和重庆城乡调查,头一站就选定武汉。
出发前一周,我不揣冒昧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秘书黄莉发微信:第一,朱玲打算给张先生和董老师扫墓,希望确知墓地方位;第二,意欲拜访谭慧老师;第三,造访者中既有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也有课题组的老伙伴,大家都乐意去华科大“走亲戚”。小黄很快回复一份编排妥当的活动日程表,还把参加人员和派车事宜交代的一清二楚。如此厚待怎不令人喜出望外、感激不尽?
3月14日(星期天)一大早,小黄带我们会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姚遂博士、张先生的女儿张鹃和经济学院的新老朋友,先后去张先生和董老师墓地献花。我们还祭奠了武大经济系教授谭崇台,他是谭慧老师的长兄,与张先生葬在同一个墓园。曾老师祖籍湖南,好友和学生遵照他的遗嘱把骨灰撒进了湘江。我清楚地记得,曾老师请谭先生为研究生班讲授专业英语。开场就是一篇英文期刊的发展经济学论文,让我们弄明白何为增长何为发展。当我站在墓园回想过往的那一刻,顿悟古人为何推崇“慎终追远”。人生有限学术无涯,个体的学术生命只有通过思想的传承和发扬而延续,这便是学术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吧。

基金会和华科大经济学院同仁携着温厚的亲情,让我们团队领悟了学术传统教育的魅力。扫墓归来,就见谭慧老师和汪小勤在贤达楼会客厅等候,欢声笑语霎时间响成一片。谭老师依然那么娴雅端庄,张鹃打趣:“妈妈为这次见面提前做了头发还化了妆!”我在感动之余也学了点待客之道。贤达楼是张先生的故居,现已修葺成一座小巧玲珑的纪念馆,室内墙壁挂满张先生的老照片,极富年代感。从惬意的露台望去,张先生多年前参与规划和施工的楼群道路尽收眼底。

谭老师耐心地等我们参观完毕,才不慌不忙地引领大家到会议室座谈。老人家打开笔记本直言,非常高兴朱玲一行来访,头天晚上为准备会话几乎失眠。不安瞬间掠过我眼底,随即发现她丝毫不显疲态,不紧不慢地讲述张先生的学术经历。谭老师深情地谈到,陶孟和先生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他们奠定的学术基础,要靠一代一代的经济学人传承下去。第一,要静下心来做学问,不要浮躁。第二,既不讲空话也不说大话,踏踏实实做调查。第三,要组织团队,经常在一起座谈,交流学问。张先生一辈子都像老黄牛一样努力,思考怎样使中国摆脱贫穷、富强起来。他的爱国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参见经济所网页:《坚持调查立所,传承学术报国-朱玲课题组在武汉祭奠经济所前辈张培刚、董辅礽》,http://ie.cssn.cn/academics/academic_activities/202103/t20210315_5318114.htm)。
为表感激,我们团队赠送华科大同仁专著一部:《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制度实验:国有农场变迁之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谭老师微笑着强调,农业很重要,张先生一辈子都重视中国农业现代化。基金会回赠我们团队每人一本张培刚画册,一本带有中文引言的张先生专著《农业与工业化》,(英文,中信出版社,2012)。姚遂和小黄还贴心地为我们接下来的调研减轻行装,把赠书打包快递经济所图书馆。
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谭慧老师和华科大朋友们的深情厚意还在我心中回荡。借此机会,我衷心祝贺基金会30周年生日,感谢基金会和经济学院甘做纽带和桥梁,把四面八方的经济学人集结在一起,齐心高扬张培刚为代表的学术传统。今后,让我们共同努力!
(2022年6月20日,北京)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