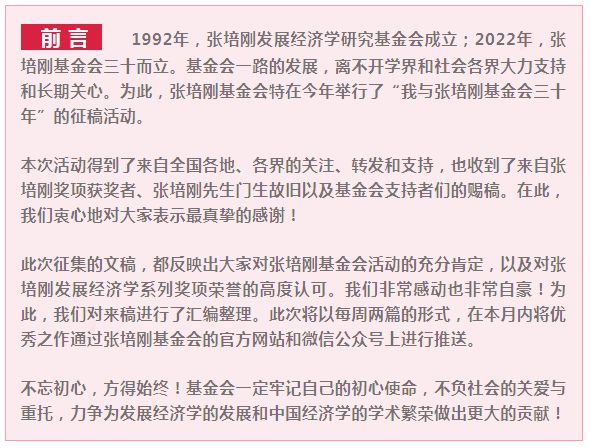
纪念吾师张培刚
汪小勤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荣誉理事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22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建会30周年。基金会以张培刚先生的名字命名,以传承和发扬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在庆祝基金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与张先生相处的点滴回忆涌上心头,提笔写下这些纪念的文字,以表达对恩师的无尽缅怀。
初识张先生
我和张老师相遇于大学英语课堂。
改革开放前夕,华中工学院老校长朱九思预见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迎来大发展,学校急需补充师资力量,于是做出了自办师资班的决定。我是华中工学院1977年招收的社会科学系第一期师资班10位学员之一。学习的课程包括英语、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外国经济学说史、《资本论》、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当听说英语课将由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位老教师来授课时,我不由心生疑虑。此前,我曾在资料室见过这位老师,印象中他比一般教师年龄稍长,常独自一人进出资料室。资料室老师曾神秘地介绍说:“这位老先生可不简单”。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位老先生似乎还未“解放”,一位被边缘化且未受重用的老师,会有什么“不简单”呢?就这样,我怀着一种复杂心情即将与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相遇。
记得第一堂课,张老师开场就说,“英语是一种语言工具,学好英语能开拓我们的视野,将来大有益处”。接着,为做到教学上“有的放矢”,张老师在正式讲课之前,对全班进行了一个摸底测验,发现班上同学的英语基础参差不齐。张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英语课程教学使全班每一位同学,包括英语基础相对薄弱同学的学习成绩都能得到提高。为此,张老师不仅讲授大学英语教材内容,还不时补讲高中英语基础知识,与此同时,还鼓励和提倡大家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英文原版读物。经过张老师“因材施教”,全班同学的英语学习果然都有明显进步和提高。
此外,张老师的英语水平和能力以及教学方法远出乎我们意料。他不仅教授北京大学编写的《大学英语》(文科适用版)教材的内容,还教给我们许多学习方法、规律和技巧。他强调,一是要记忆而且要会读会写足够的单词量(5000以上),二是熟练掌握各种句型、时态、语态的使用,再就是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他把英语学习比喻为用石、沙、砖头以及钢筋水泥盖房子的过程。他还教我们如何根据英语单词中的词根,以及前、后缀来判断词意、以及阅读和发音,并帮助记忆和扩大词汇量等。他还通过讲解中英文人名和寄信地址等书写的不同特点,比较和发掘背后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英文人名的书写特点,是先写“名”(given name),后写“姓”(family name);英文信件的收发信地址,也是先写人名,再写街区、市县、州(省)名,最后写国家的名字,而中文的人名和信件地址的写法刚好相反。这两种写法有什么文化意义呢?张老师说,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西方文化比较突出个人价值,强调个人独立性、自主性、优先性,所以个人的名字写在前面;中国文化更提倡“家国情怀”,强调个人与家庭、民族和国家的隶属与共生关系,所以最后才写个人。
张老师操着略带湖北口音的英语,把英语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张老师上课,旁征博引、学贯中西,常常给人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的感觉。张老师把英语课讲“活”了,张老师的课深受大家喜爱。
张老师的教学一丝不苟,每次英语作业本发回来,都可以看到张老师在每一个同学练习本上用红笔修改后的密密麻麻的印记,如单词拼写错误,大小写、冠词和不定冠词使用不当,词序及语句顺序,以及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问题,甚至标点符号、英语书写格式规范等等,都是他认真、细致批改的痕迹。记得学完北大编的《大学英语》(第一册),我们就进入英语复习考试。由于平时我作业中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小错误,这一次考试我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争取考一个满分。不料,最终还是因为一个标点符号错误扣了两分,虽然心中有些遗憾,但张老师对工作和事业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日后收益良多。
张老师不但工作严谨、认真,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他喜欢看各类球赛、听音乐会,读武侠小说。记得当时张老师家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每当有好的球赛和文艺节目,我们班同学晚上就去张老师家看电视,虽然房间里十分拥挤,但师生一起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张老师听说在学校西边体育馆,晚上有一场我们班两个女同学代表校队参加的篮球比赛,他就带着小凳子,兴致勃勃地独自一人去看球赛,当拉拉队员助威。当场地的管理人员发现一位老教师坐在球场边正在观看比赛,吓得赶紧把他搀扶到运动员坐席上,生怕飞过来的球砸着了老人家。
1977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张老师前往北京参与《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写工作,不得已中断了我们的英语课教学,令同学们无不感到失落和遗憾。
1979年暑假,趁着全班同学赴延安革命老区考察并路过北京的机会,我作为学生代表和几位老师一起去看望正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紧张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的张老师。只见老师住在早期的苏联专家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套桌椅,桌子和床上放满了参考书,洗脸池还浸泡着没来得及清洗的衣服,条件看上去十分简陋。张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还请我们在附近月坛北小街的成都饭庄吃了一个“便饭”,席间张老师和蔼可亲,与我们交谈甚欢。
尽管大学时期,张老师只给我上了一门英语课,但张老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态度,特别是对来自农村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同学的仁厚、关爱和悲悯之情,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久远。
再识张先生
师资班刚一毕业,张老师就介绍两个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去到武汉大学经济系旁听三门课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的第一堂课,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周新民自我介绍道:1940年,他以清华大学经济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来,根据过往经验,清华大学许多专业第一名的毕业生可直接保送清华庚款公费留学。但就在当年,该项目改为面向全国公开招考。也就是说,无论清华或非清华毕业生,无论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各专业考试成绩第一名者即可获得清华庚款公费留学机会。显然,对周新民等清华大学应届生而言,竞争激烈程度陡然增加。不过也有同学说,尽管说是全国公开招考,但就经济学科而言,周新民真正的竞争对手只有一位,即从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的张培刚。但张培刚大学毕业已有6年,在专业课考试、尤其是英文写作方面,作为应届毕业生周新民应更有优势。然而,当周新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看榜单揭晓时,张培刚的名字赫然在列。落榜后,周新民不得不选择第二年继续报考。周新民教授还说,“这位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张培刚,曾经是我们武大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现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听到这里,我和同学黄红云十分惊喜。回来后我就去问张老师:“这是真的吗?”,张老师微笑着说:“如果他(指周新民教授)是这么说的,那就是吧”。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考取张老师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着北美、拉美、欧洲,澳洲、以及亚洲和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纷纷来访,张老师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些学者中包括哈佛大学经济系前系主任帕金斯教授,美国罗杰斯大学杜塔教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杜伊斯堡-诶森大学)卡塞尔、何梦笔、费多丽、陶伯教授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戈登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顾应昌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杨小凯教授,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以及台湾大学施建生教授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先生,还有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回大陆求职的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等。这些学者教授和张老师建立了频密的学术交流关系,成立学术论坛和举办学术会议,并互派访问学者等。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有幸参与其中许多学术交流活动,并在张老师的推荐下,获得多次出国学术访问机会。在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发现,除了极少数学者(如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顾应昌教授、台湾大学经济系施建生教授曾是张老师早年的哈佛同窗)外,大多数学者从未与张先生谋面,但他们似乎对张老师早就十分了解,对张老师非常尊重。我想这一定是张老师早年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所致。
其中,令人难忘的,是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顾应昌教授的来访。在一次和研究生的座谈会上,顾应昌教授连续问我们在座的同学:“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吗?”,“你们知道你们和谁在一起学习和共事吗?”,见我们一时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如果你们培刚老师不回国,他就该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人了(注: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在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者),不是刘易斯、舒尔茨”。此话令我们十分震惊。虽然那时,我正在研读张老师的《农业与工业化》,也知道张老师博士论文得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的荣誉。同时,我也研读了包括刘易斯、舒尔茨等人在内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和著作,并且发现,和许多发展经济学经典文献比,张老师《农业与工业化》的问世时间更早,研究的主题更宏大、意义更深远,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更具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仍未想到张老师的学术成就竟如此之高,更没想到张老师回国,竟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顾应昌先生还说道,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几位华裔经济学教授,大量运用了张老师《农业与工业化》中的理论和思想,为台湾农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建言献策。我想,这也许是顾应昌先生如此景仰张老师的原因吧。张老师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只可惜,“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历经30多年的坎坷之后,张老师《农业与工业化》的中文版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并逐渐为人知晓。
此外,顾应昌教授还谈到另一件事。众所周知,S.库兹涅茨教授曾因运用统计学方法,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建立以及各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从未涉足农业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教授,于1960年代出版了一部关于农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书籍。在该书中关于农业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与张老师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相关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整部书中没有任何引用和参考的指示和说明。顾应昌教授说,这就是剽窃张先生的研究成果,是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他还说,只要培刚先生同意,他和几位美籍华人教授就会代表张老师在美国和库兹涅茨打官司。当我听到“打官司”一词,不禁吓了一跳。可见,这件事在他看来有多么严重。可是,当我问张老师:“您知道这事吗?您打算和库兹涅茨打官司吗?”张老师只是微笑着摇摇头,他并不打算追究和计较。我又问说,“听顾应昌教授讲,如果您不回国,就可以得诺贝尔奖。您后悔吗?”张老师说,他不后悔。在如此重大的得失面前,张老师竟如此淡定、决绝,处之泰然,令我等晚辈无比敬佩。
是的,也许至今仍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但我坚信张老师真的不后悔。因为,他早年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报效祖国,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是为了中国人尤其是广大贫困的农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张老师当初获得庚款赴哈佛大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抵达后的学习使张老师发现这个专业太过微观,倒是有利于个人发财致富,但与他原先的抱负和理念相去甚远。因此,张老师坚决要求转到更为宏观、更偏重理论研究,当然,学业完成的困难度也更高的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宏大课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实现他早年离家求学,从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直至出国深造,到最后归来报效祖国的夙愿。可见,在张老师的“辞典”里,根本没有“如果不回国,就……”这样的虚拟语句。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悔”二字。正因如此,张老师才取得如此傲人的成就。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相信,没有远大的抱负作为精神支柱及支撑,任何事业都走不远。
张老师不仅是一位学术大师,也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充满感情,对生活充满热情,立体、多面、生动,且有趣的人。遇见张老师,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张老师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人生楷模和价值标杆。在我心中,张老师亦师亦友、亦师亦父。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走笔至此,思念之情,汹涌而来,泪不自禁。
感念张老师晚年的世纪追问: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经济发展向何处去?忧从中来。
张老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引领我的人生。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
基金会公告
更多